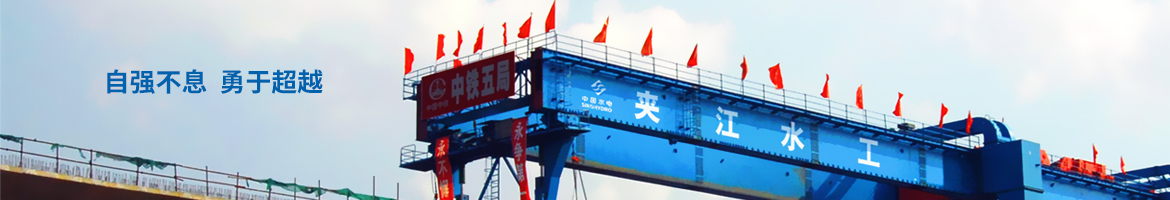【走过60年】电流声中的匠心 | |
| |
“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,谢师傅教我电气设施的安装工作,他嘶哑的咳嗽声混着机器的声响,像台老旧的柴油机在发动。”杨朝晖眼角的皱纹里漾起涟漪——今年是他与夹江水工相伴的第32个春秋。 杨朝晖在防腐检测 机油味里种匠心 1993年春,22岁的杨朝晖义务兵退伍,在夹江水工原动力车间电工二班上班的第一天,谢贵和师傅递给他一副绝缘手套,袖口还沾着新鲜的机油渍:“干电工,手要稳,心要细。” 这个烟瘾极大的老师傅有个标志性动作——每隔几十秒就会爆发出一阵沙哑的咳嗽。本就紧张的杨朝晖在拧瓷瓶螺帽时被咳嗽声惊得手一抖,“咔嚓”声里瓷瓶迸裂,琥珀色的变压器油喷涌而出,瞬间浸透了蓝色工装。他僵立在梯子上,指尖还保持着拧动的姿势,耳中只余自己咚咚的心跳声。 “下来吧,小伙子,”谢师傅的声音出乎意料的温和,布满老茧的手掌拍了拍他的肩膀,“怕犯错是好事,但干活一定要沉下心,不能慌,每个环节都关系设备的安全运行。” 从那以后,杨朝晖时刻谨记师傅讲的每句话。当同期进厂的年轻人抱怨电工活又脏又累时,他总在油污里跪得笔直,仔细安装电气设施。 后来任班长那天,谢师傅拍着他肩膀:“全车间数你最细致,连螺丝帽都跟拿尺子比着拧似的。” 跨越山海磨匠心 杨朝晖(右一)获评三峡北线船闸2024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劳动竞赛“先进个人”称号 2002年盛夏,钢板晒得能煎熟鸡蛋。杨朝晖作为电工二班班长,厂内组织三峡门机的电气制造——这是他第一次碰国家级工程,接线时连呼吸都轻了三分。“小杨,这几个端子接线差口气。”业主的话让他后背发紧,他蹲在地上盯电线走向,膝盖麻了就踮着脚,工装被汗泡得能拧出水,汗珠砸在金属上“滋”地成烟。油污擦花了视线,他就用袖口抹一把,手臂抬不动了,甩甩酸麻继续接,硬是加班改到每个接头都像列队的士兵,顺利通过验收。 这份“差毫厘都不行”的劲,让他2006年拿下夹江水工技能比武第一,捧回电工技师证。可真正的考验在2005年小湾工地——云雾裹着陡峭山崖,600吨斜拉式门机是当时世界之最。山风卷着雨丝打在脸上,钢结构表面滑得站不稳。深夜缩在床上,山风从缝隙钻进来呜咽,放弃的念头翻来覆去——直到晨光刺破云雾,照在门机的巨臂上,他摸出兜里谢师傅送的旧手套,忽然就定了心。六个月里,他改数据改到手指起茧,终于和同事在云雾里立起“世界之最”,那山风的呼啸,成了他最难忘的成长背景音。 后来去巴基斯坦砀萨工程、尼杰电站,语言不通就用蹩脚英语比手势,文化不同就跟着当地工人学习风俗。湿热气候里,他顶着中暑的风险教操作;地质复杂时,他带头排查隐患。当设备终于转起来,他布满血丝的眼里,亮的不只是成功的喜悦,还有中国工匠跨过高山深海的坚守。 多重角色守匠心 2011年兼职安全管理,杨朝晖心里像揣了块烫铁:“电工错了是机器坏,安全错了是人命关天。”每天清晨,他总是第一个到工地,沿着固定路线查隐患,班前记录本上的字比电线还密。同事笑他“查安全比CT还细”,可正是这份细,让大家干活时格外安心。 2016年夹江水工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,他把每个流程拆成“螺丝扣”,将身为电气人的细致严谨发挥到极致。 2018年拿到注册安全工程师证时,他的笔记本每一页已经记满了“以人为本”的实在话。 2020年转检修项目,智能化浪潮拍过来,50岁的杨朝晖成了“老学生”。深圳地铁智能门机的程序像“天书”,他就追着年轻工程师问,把操作细节记在手机备忘录里,调试时站在机器旁盯一整天。2022年智能门机顺利运行那天,年轻技术员围着他竖大拇指,他挠挠头笑:“我就是笨办法,多学多练呗。” 同年扎进三峡船闸防腐工程,“长江咽喉”容不得半粒沙。他爬几十米高的钢架,用仪器量每一寸金属表面,焊缝里的锈迹都要抠干净。三年来,100多篇工作周报写得工工整整,照片下的备注比说明还细——就像他的人,不张扬,却把严谨刻进每个标点。 机器轰鸣的电站里,杨朝晖还有个“秘密”——他爱用镜头拍风景。清晨薄雾给门机镀金边,傍晚晚霞把江面染成金波,雨后彩虹跨在天边——这些转瞬即逝的美,都被他存进相册。“干活要细,生活要暖。”他总这么说。长江的涛声里,他左手握扳手筑安全防线,右手举相机记生活美好,责任与热爱,在他眼里都闪着光。 杨朝晖镜头里的三峡大坝 三十二年,是夹江水工半程的历史,却是杨朝晖从青丝到华发的全部。他看着企业从国内走向国际、从传统迈向智能,自己也从瓷瓶碎裂时慌神的年轻人,长成能在万吨门机上写传奇的守护者。谢师傅的咳嗽声、三峡的轰鸣、小湾的山风……都成了他故事里的韵脚——而这故事,也是无数水电人用青春织就的梦。 杨朝晖就像水电事业里的一颗星,不耀眼,却执着地亮着。他用三十年时光,在钢铁与江河间,写下属于中国工人的“匠心诗篇”。(责任编辑 蒲玉凤) | |
|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 |
| 浏览次数: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