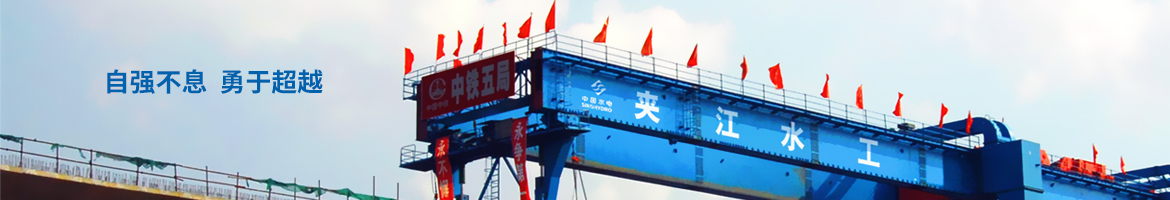【走过60年】铆工的硬核浪漫 | |
| |
编者按:六十载风雨兼程,一甲子春华秋实。当岁月的指针回拨,一代又一代的夹江水工人,在隆隆的机器声中默默坚守,在泛黄的图纸前精益求精,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劈波斩浪,与国家发展脉搏同频共振,在时代大潮中刻下深深印记。水电七局成立六十周年之际,夹江公司开展“走过60年”主题征文活动,邀请所有亲历者、见证者、建设者,翻开记忆的相册,执起深情的笔触,讲述那些与江河为伴、同山岳共舞的峥嵘岁月,描绘那热火朝天、激情燃烧的建设图景,刻画平凡岗位上可敬可爱的身影,抒发对事业薪火相传、继往开来的真挚情感与深邃思考。征途如虹,江河见证;未来可期,笔墨同行!本网将陆续刊发征文作品,以飧读者,敬请期待。 我叫李彭,夹江水工的一名铆工班长,一名扎根一线的“九五后”蓝领工人。三十而立,回望来时路,从技校实习生的懵懂起步,到如今肩扛班组重任,十五载光阴,竟已悉数交付给了钢铁。这双手,丈量过、编织过二十余座国内外水电站的数万吨钢铁“筋骨”——“铆工”二字,不仅是我职业的起点,更是我青春与理想的熔铸之地。 19岁的李彭 铆工是金属诗人:在刚与柔之间谱写工业美学 铆工,一个常隐于焊光弧影之后的工种,宛如工业体系中的“秘密花园”,鲜为外界所知。在许多人眼中,我们的工作或许止于“抡大锤、拼钢板”。然而,其内核远非如此粗犷。从图纸工艺的精确解读、来料尺寸的严苛把关,到复杂构件的空间放样、精密拼装,再到焊接变形的实时监控、焊后精密的修校打磨……铆工,是贯穿金属结构成型全程的“钢铁裁缝”。但我更愿称我们为“金属诗人”——当两个铆工的视线在经纬仪与水准尺间精准交汇,当烤枪在钢板上描绘出温度的诗行,当坚硬的钢铁在技巧下展现不可思议的柔韧,当巨型部件如古老榫卯般严丝合缝……那一刻,我们正以钢铁为笔,以汗水为墨,在水电工程与装备制造的宏阔画卷上,书写着最硬核的现代工业诗篇。 犹记21岁那年,挑战加拿大莫斯卡特项目——夹江水工叩响高端金属结构市场的“第一张名片”。面对精度要求远超发丝直径的极限挑战,我与团队首创“温度-应力-形变”动态平衡法。当几十吨重的巨型闸门在我们的精心“缝制”下严丝合缝,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工业美感时,那份自豪难以言表。最终,项目以欧美标准百分百合格率通过外方监理验收。那高高竖起的大拇指背后,无人知晓是数百个日夜的技术研讨、无数次细微至毫厘的温度调试,是钢铁在皮肤上烙下的淤青印记、是汗水反复浸透又风干的工装……这是我们铆工对极致工艺近乎偏执的无声追求。 李彭工作中 铆工是硬核乐高高手:毫米级精度下的高空舞蹈 “你见过在空中拼装巨型乐高吗?”——这并非科幻场景,而是铆工的日常。业内戏言:“不会‘上天’的铆工不是好铆工。”我的首次“上天”经历,是参与组装当时世界最大起重容量的溪洛渡水电站8000千牛门机。那时毕业仅一年,自诩见过些“世面”,但当真正站在离地二十多米、尚在“生长”中的“半成品”门架上,身体连同安全绳都随着结构的每一次轻微晃动而震颤。天车吊装的巨大部件精准就位时的轻微碰撞,瞬间传递的震动几乎将我“晃”下高空,那一刻的惊心动魄,至今刻骨铭心。 溪洛渡水电站8000千牛双向门机厂内预拼装 如今,经手拼装的门机、桥机、弧门、闸门不计其数,积累了丰富的“高空搭积木”经验,动辄数吨的部件在手中驯服。然而,“安全”这根弦始终紧绷如初。“高高兴兴上天来,平平安安下地去”,是我带领班组成员作业时恪守的铁律。 我们拼装的“乐高”,块头惊人,精度要求却苛刻至毫米级。以正在攻坚的世纪工程——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的平陆运河项目为例。其执行的是超越行业规范的“平陆标准”。几十米长的庞然大物,拼装误差须控制在1毫米以内!要求平直的部位,一把钢尺贴上去,必须严丝合缝,不容丝毫间隙。这绝非寻常积木可比,是门槛极高的“硬核”挑战。连我那经验逾三十载的老师傅,也常感叹于此行“活到老,学到老!”。 今年6月初验收通过的长178米、重500吨的平陆运河项目台车梁桥 当诸位仰望三峡大坝巍峨耸立的巨型门机,那钢铁的骨骼深处,镌刻着我们铆工默默奉献的青春印记;当你们为白鹤滩水电站开闸泄洪的磅礴气势所震撼,那轰鸣的水声中,激荡着我们凝结于每一条精密焊缝中的奋斗誓言。 十五年,从技校生成长为青年岗位能手,从农村娃蜕变为优秀共产党员。我用光阴作刻刀,在厚重的钢板上,一笔一划深深刻写着“铆工”的职业荣光。那些被汗水反复浸透的图纸,那些被焊花点亮的不眠长夜,那些在重型机械轰鸣声中迎来的晨曦……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一代青年铆工最硬核的成长图鉴。 传承工匠精神,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新作为、新担当,是我们的使命。未来,我将继续在这钢铁经纬间奋力书写,为锻造企业新质生产力,贡献属于我的、滚烫的青春与力量!(责任编辑 蒲玉凤) | |
|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 |
| 浏览次数: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