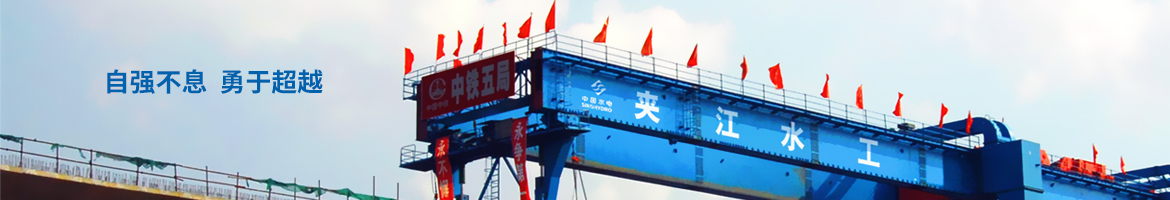雪落无声时 | |
| |
这南方的土地,是“吝啬”的,它慷慨地赠我以终年的青翠,与湿润的暖风,却独独扣住了我生命里最熟悉的那一片凛冽与洁白。我的大西北,就在昨夜,在晚秋的尾音上,悄然披上了它今年的第一件银裳。 照片是从母亲的手机里渡过来的。一帧一帧,像沉默的信使,在我这四季常青的异乡,投下几枚冰凉而温柔的炸弹。炸开的是满眼的惊叹,更是心底一片汪洋的乡愁。那是我多么熟悉的天地啊!远处的山峦,失了春夏的棱角,被雪温柔地勾勒出浑圆的轮廓,像沉睡的巨兽安详的脊背。近处的屋瓦,红白分明,红色的线条是岁月坚韧的骨骼,白色的积雪是自然一时的抚慰。院子里那棵花椒树,枝丫虬结,此刻每一根细小的枝条都托着一条茸茸的、胖胖的雪,像是忽然开满了银色的花。世界静极了,静得仿佛能听见雪花簌簌扑向大地的、那比叹息还轻的声响。这屏幕里的静,与我周遭车水马龙的喧嚣一撞,便生出一种令人心慌的隔膜来。 我的魂灵,便从这南方的温润里,倏地一下,被吸回了那照片中的世界,落座在那小小的、暖烘烘的土房里。 这便是我过分奢侈的梦了——落雪的日子,一家人围着火炉。那炉子,是西北人最留恋、最亲切、也是家的心脏。通红的光跳跃着,映在父母日渐深刻的皱纹里,竟也将那沟壑熨帖得柔和起来。炉火“呼呼”地响,是这屋里最安稳的背景音。炉盘上,坐着一把被烟火熏得乌黑的茶壶,嘴里吐着白汽,“咕嘟咕嘟”,是幸福的呓语。父亲的罐罐茶,正熬到浓酽的时候,那苦苦的、涩涩的香气,与枣子的甜香缠绕在一起,弥漫了整个屋子,是嗅觉里关于“家”最牢靠的定义。 炉灰里,埋着几颗洋芋。围炉者耐心地等着,用火钳不时地去拨弄。直到那层焦硬的外皮“噗”地裂开一道口子,露出里面沙糯的、金黄的心。母亲用满是茧子的手,不怕烫地捡起来,在两只手里飞快地倒替着,吹着气,为我剥开。那股混着草木灰与粮食本真的焦香,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比拟的。我捧着那块滚烫的洋芋,像捧着一小颗太阳,从指尖一直暖到心里。 我们便这样坐着,喝着滚烫的茶,吃着香甜的洋芋,说些闲话。话头是散的,东家长,西家短,今年的收成,明年的打算。父母的笑声,是那样朴实而敞亮,在小小的屋子里碰撞。窗外的雪,无声地落,将我们这方小小的温暖,衬托得像一个被世界遗忘的、却无比安全的孤岛。那时的我,只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寻常,何曾想过,有朝一日,它会变成一种需要隔着千山万水去眺望的、不敢轻易触碰的奢侈。 这奢侈,一年,只有一次。像候鸟的迁徙,我回到那片土地,回到他们身边。可每一次回去,都仿佛看见时光在他们身上又刻下新的痕迹。父亲的背,好像更驼了一些,那罐罐茶端起来时,手会有些微的颤抖。母亲的白发,是任何染发剂也遮掩不住的了,它们倔强地从鬓角钻出来,像故乡山头的雪。而我,能做的太少,陪伴的时日太短。那一年一度的团圆,在三百多个分离的日子里,像夜空中偶尔炸响的烟花,绚烂一瞬,便沉入更深的寂寥。这短暂的欢愉,偿还不了漫长的缺席,反倒生出更深的愧疚来,沉甸甸地压在心头。 故乡的雪,落在地上,是静谧的;落在我心里,却是有声的。那是我童年踩雪的“咯吱”声,是火炉的“呼呼”声,是茶壶的“咕嘟”声,是父母谈笑的声音。这些声音,在南方无数个无眠的夜里,汇聚成一条喧哗的河流,将我淹没。 雪,还在照片里静静地白着。我的思念,却像那熬过头的罐罐茶,又浓,又苦。这南方的天空,何时能懂得,一个游子对一片雪花的渴望呢?那渴望里,是整整一个故乡,和故乡里,那两位日渐老去的、我生命中最温暖的火光。(责任编辑 蒲玉凤) | |
|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 |
| 浏览次数: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