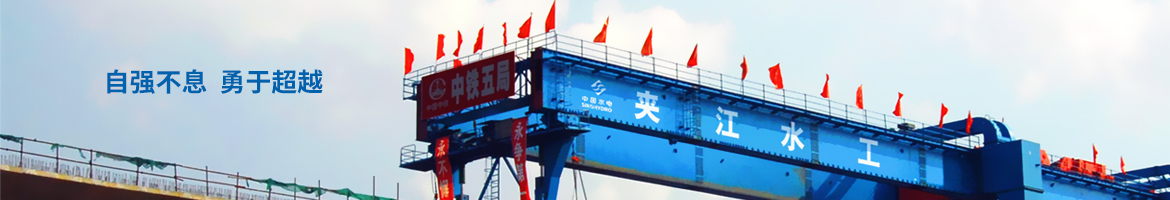书痕 | |
| |
我的姥爷,是农业社里的会计。在那片被黄土厚厚覆盖的高原上,识字的人本就不多,像他那样不仅能拨算盘、记工分,还写得一手好字,甚至能画几笔山水、刻几方印子的人,就更如凤毛麟角了。他那些视若性命的书,大多是用鸡蛋、粮食,从那些摇着拨浪鼓的货郎担上,小心翼翼地换来的。在那些贫瘠得连风都带着干土味的年月里,书是比油盐还要金贵的东西。他不读的时候,总是将它们一本本抚平,再悄悄地锁进那只厚重的、散发着陈木气息的柜子里。我至今还记得那些书的模样:内页是沉甸甸的焦黄,书皮是用粗糙的麻纸仔细包裹的,上面是他用毛笔写下的书名,字迹清瘦,筋骨分明,隔着岁月,依然力透纸背。 小学三年级的暑假,是在姥爷家度过的。黄土高原的夏日,夜晚总算是凉爽的。我最期盼的,便是夜里躺在凉爽的土炕上,听姥爷讲故事。姥姥总是安静地坐在炕尾,或许那些故事她已听过许多遍,或许也有她不熟悉的,但她总是不言语,只是耐心地听着,手里的针线活有一搭没一搭地缝着,直到眼皮沉沉地阖上。姥爷则靠在炕头火炉边,身下垫着一块圆形的、被烤得分辨不出颜色的木板,那是他放烟袋家什的地方。可他讲故事时是从不抽烟的,他怕那烟灰落下来,污了书的洁净。直到故事讲完,我们都沉入梦乡,他才窸窸窣窣地点起那杆长长的烟锅,橘红的火星在昏黄的灯泡下一明一灭,映着他沉默的、望向虚空的脸。 然而,那个夏天也发生了一场风暴。孩子的叛逆心,像高原上无端刮起的狂风,不知怎么就占据了我。许是觉得姥爷只顾看书冷落了我,我竟赌气地提起他桌上的毛笔,在他正读着的一本书上,胡乱画了好几页。那瞬间的破坏欲带来的快感,立刻被巨大的恐惧淹没了。姥爷回来看到,先是愣住,随即,我从未见过他那样“发疯”,他平日里温和的脸庞因震怒而扭曲,顺手抄起炕笤帚就向我冲来。我吓坏了,像一只被猎人追赶的野兔子,头也不回地冲出院子,翻过了屋后那座沉默的、在月光下泛着青灰色光晕的大山,一路跑回了自己家。 我没敢告诉父母缘由。直到半夜,迷迷糊糊中听到院门响,接着是姥爷和大舅压低了的、带着喘息的声音,他们在问母亲我是不是回来了。母亲这才恍然,连声应着。我躲在被窝里,听见姥爷用他那带着黄土味道的方言,很不好意思地对我父亲说:“娃娃跑得急,我不该追的……”那句话隔着门帘传进来,轻飘飘的,却像一把锤子,重重地砸在我心上。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,不是委屈,是悔恨。那一刻,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白,那些发黄的书页,在他心里究竟有多重。 许多年后,我大学毕业,参加了工作。姥爷的眼神早已不好使了,看东西总要凑得很近。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,给他买了一套他最钟爱的、也是市面上能找到的最全的《水浒传》。他接到书时,那双浑浊的眼睛里,竟又闪出了我童年时见过的、如获至宝的光。他依旧像从前那样,用袖子拂去并不存在的灰尘,然后郑重地、将它们一一锁进那只老木柜里。往后的日子,我便常见他坐在午后的阳光里,举着一面大大的放大镜,一字一字地,极其缓慢地移动着,仿佛要在那字里行间,找回他逝去的、明亮的世界。 聚少离多,是黄土高原上所有离乡子弟共同的命运。时间是最无情的摧折,它最终带走了我的姥爷。 当他真的离开后,我恍惚地回到那间老屋,用那把熟悉的、已有些锈迹的钥匙,打开了那只木柜的锁。柜门开启的刹那,一股熟悉的、混合着墨、纸、木头和老屋气息的味道扑面而来。里面,书籍依旧码放得整整齐齐,那套我送他的《水浒传》崭新如昨,旁边,是那些我曾涂抹过的、被他用白纸细心裱糊好的旧书。物依旧,人已非。 那一刻,我所有的坚强被瓦解。黄土高原的风依旧在窗外呜咽,吹拂着千沟万壑,却吹不散这柜中凝结的、一个普通农人对文化最朴素的渴望,一位长辈对孩子最笨拙也最深沉的爱护,以及一个外孙女,对远去的光阴与亲人,那无边无际、无处投递的思念。(责任编辑 蒲玉凤) | |
|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 |
| 浏览次数: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