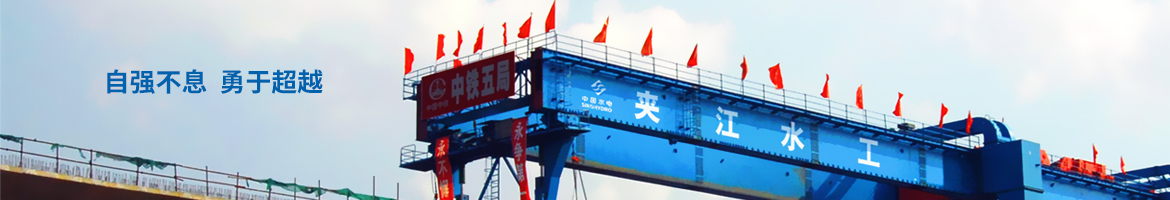炊烟升起的地方 | |
| |
这灶台,是黄土高原的心脏,是家家户户的命脉。它敦敦实实地踞在屋角,用一身的热量,撑起了一日三餐,也撑起了一个家的魂魄。我总觉得,那被烟熏火燎得黑亮黑亮的灶膛里,燃烧的不仅是柴火,更是密密匝匝的日子,是西北人那沉默而坚韧的性命。 我家的灶台,也经历了几番变迁。最早的记忆,是黄泥巴糊的,侧面还有麦壳,却有一种朴拙的温存。后来,换成了砖头砌的,水泥抹的,最后还贴上了光洁的瓷砖,瞧着是齐整了,亮堂了,可我总觉得,那泥灶的魂儿,似乎也随着那光滑的瓷面,一丝丝地淡去了。然而,任凭形貌如何更迭,灶台前那忙碌的身影,却一代一代,未曾变过。 那些实实在在属于妇女们的舞台。我的奶奶,便是在这舞台上,演完了她大半个人生。我总记得她移动着那双被裹得尖尖的小脚,在灶台与案板之间,来来回回地盘旋,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陀螺。风箱在她手边“呼嗒、呼嗒”地响着,那声音沉沉的,闷闷的,像是岁月深长的叹息。火苗随着那节奏,一明一暗,映亮了她满是皱纹的脸。那脸上,没有悲,也没有喜,只有一种认命似的慈和。她能用什么呢?不过是些土豆、白菜、粗砺的杂面。可就是这些有限的食材,经了她的手,便在锅里有了光景,成了养人性命的、热腾腾的饭食。那手艺,不是技艺,是本能,是土地赋予女人最原始的神通。 母亲是接着这舞台的人。她比奶奶健朗,从地里归来,带着一身黄土的气息,便又立刻扎进这灶火的温热里。锅碗瓢盆的碰撞声,是她匆忙的序曲。我那时还小,够不着那高高的大案板,便垫着小木凳,踮着脚,学着她的样子,笨拙地擀着面。那面团在我小小的手里,总是不听使唤,而灶洞里,麦秸噼啪,树枝哔剥,后来条件好了,也烧过煤,那红彤彤的火光,是一样的暖。它们都尽了自个儿的本分,将一身的热,毫无保留地熬煮出来,成全了锅里的饭菜,也成全了我的童年。 记忆中我曾经打破过一口缝补多次的老铁锅,是菜刀跌落铁锅引起的,那一声碎裂,惊起的不是呵斥,是奶奶眼中倏然黯淡的光,是母亲嘴角微微一颤又迅速压下的心疼。可她们最先修补的,不是灶台,是一个孩子受惊的心。这份沉默的宽容,比任何责备都更沉重地烙在我心上。往后的岁月里,我见过许多光洁现代的灶具,却始终忘不了那个烟火熏黑的土灶台——它教我懂得,西北农人对生活的眷恋,就凝在那一锅一灶的温度里;而最深的爱,往往是破碎时那声无言的叹息,和叹息之后,依然为你捧出的那碗热汤。 让人难以忘却的永远是那缕青烟,那一缕青灰色的烟,悠悠地、怯怯地探出头来,随即胆子便大了,成股成团地涌出,在空中一下子散了形骸。它们自由自在地旋飞着,扭动着,像一群得了赦的精灵,掠过屋檐,掠过树梢,袅袅地向着更高、更远的地方去了。它们鸟瞰着脚下的村庄,鸟瞰着连绵的黄土高原的大山,那样从容,那样舒展,是我在人间从未见过的、真正的自由。我那时痴想,这烟的灵魂,或许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幸福些。 可这样的光景,终究是一去不返了。如今的村庄,是用了天然气、电磁炉,灶台早已冷清了,烟囱也寂寞了。我再也没有机会,在那宽大的锅灶前,施展一番从奶奶、母亲那里看来的厨艺;也再没有机会,看见奶奶坐在灶前,拉着风箱时那被火光映得无比慈祥的面孔了。那“呼嗒、呼嗒”的声音,成了我梦里最深、最沉的背景音。 那从烟囱里逸出的、会跳舞的烟雾,连同那灶火曾给予我的、最扎实的温暖,都一并飘散了,散在如今这过于干净、也过于冷静的空气里,再也寻不着一丝痕迹。我只余下这满腹的怀念,像灶膛里冷却的灰烬,看着是熄了,但只需一句乡音,一段旧梦,便能吹开浮灰,露出底下那永不褪色的、红彤彤的光来。(责任编辑 蒲玉凤) | |
|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 |
| 浏览次数: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