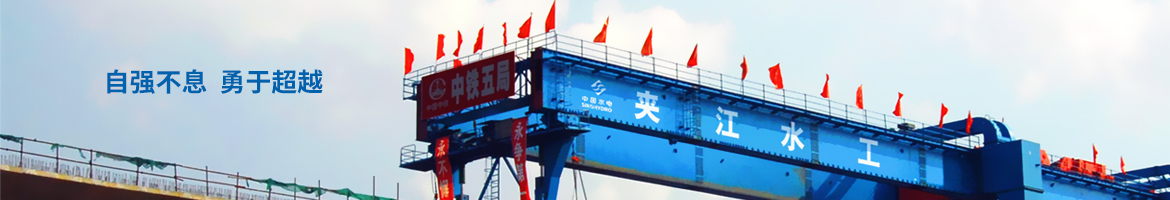霜降帖 | |
| |
我走在钦州湾的风里,看着风电塔筒一节节消缺完成,这些塔筒后续经发运吊装之后就会像大地的肋骨,将天空支得更高、更远。钦州这边也降温了,吹来海风是咸的、带着湿冷,这里的晚秋,仿佛被稀释了一般,草木依旧绿着,没有一丝疲态。直到手机上的日历提醒我,“霜降”二字跳了出来,心里才猛地一沉,像被一枚冰凉、坚硬的石子叩响了。 霜降了。我的思绪霎时间挣脱了这海边的湿冷,越过千山万水,像一只识途的候鸟,精准地投向了那片苍黄的、属于会宁故乡的土地。 那才是真正的秋天。 记忆里的风,是干爽的,带着玉米被烤熟的焦香。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,被一场接一场的霜,漂得愈发苍白而显得肃穆。田间,那一片片站立的玉米秆,就是这肃穆画卷上最后、最热烈的笔触。叶子已经黄得彻底,边缘卷曲着,在风里发出簌簌的声响,像无数张脆薄的纸张在摩擦。而最动人的,是挂在秆子上那些玉米棒子。它们的外衣被秋阳和秋霜轮番浸染成一种无法调出的秋黄色,沉甸甸的,将那原本挺拔的秸秆,也压出了一道谦卑的、优美的弧线。 那时,我和父母就在这秋黄的海洋里。父亲走在最前,用那双布满茧子和裂口的手,握住玉米棒子,猛地一拧、一掰,便传来一声清脆的“咔嚓”声。那声音,是秋天最饱满的律动。母亲跟在后头,利落地剥开苞衣,金灿灿的玉米便出来了,一粒粒,挤得那样紧实,像凝固的阳光,像大地上结出的纯金。 我的任务,是将这些“金疙瘩”扔进手里的的化肥袋子。玉米落在化肥袋子是“哗啦啦”的合唱。不一会儿,化肥袋便重得像一座小山,压得人直不起腰。汗水顺着额角流下,蜇得眼睛生疼,可心里是快活的。休息时,父亲会寻一处被风刮得干净的田埂坐下,摸出烟袋,默默地抽着。他望着堆成小山的玉米,目光里有种土地般的安稳和满足。母亲则用镰刀,削一根汁水尚存的秸秆,递给我,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甜,便能驱散一整个上午的疲累。 那时的霜降,是可以用身体去感受的。是清晨玉米叶上那层茸茸的、冰晶的白,是指尖触碰时一激灵的凉,是父亲呵出的那团看得见的白气,也是母亲在傍晚灶火前,为我们烘烤湿鞋时,那弥漫开来的、带着土腥气的温暖。 而今,在这四季难以分明的南国,所有的感知都变得模糊。我眼前的钢铁塔筒,它们未来将捕捉的风,是无形的、呼啸的能量;而故乡的风,却是有形状、有味道、有温度的,它雕刻着山塬,也雕刻着人的年轮。 闲暇时间,与老家视频。屏幕那端,是父亲愈发深重的皱纹,和院子里那熟悉的、金黄的玉米堆。我问:“爸,霜降了,咱家玉米都收完了么?” “还有一点点了,”父亲笑着,声音透过小小的扬声器传来,有些失真,却依旧带着黄土的颗粒感,“今年的棒子都饱得很。你妈正念叨着,等你回来,给你煮迟玉米吃哩。” 我喉头一哽,说不出话,只是用力地点着头。虽然挂了电话,但我知道,有一场真正的、名为“霜降”的节气,只属于那片苍茫的高原。它不在日历上,也不在气象学的报告里,它沉沉地睡在我背过玉米的脊梁上,睡在父母日渐斑白的发梢上,睡在那一望无际的、静默的、正准备越冬的黄土里。 那是我一生也走不出的、精神的故乡。(责任编辑 蒲玉凤) | |
|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 |
| 浏览次数: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