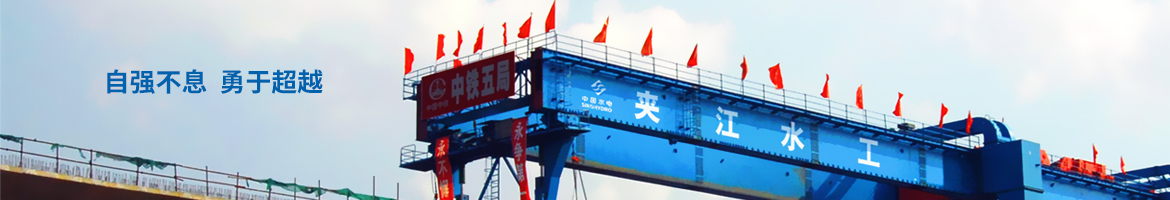停转的石磨 | |
| |
记忆深处,总有一圈圈石磨转动的声响,混着谷物破碎的清香,和奶奶低低的哼唱,在黄土高原的风里,飘飘摇摇,贯穿了我整个童年。 那盘石磨,就立在土坯房中央一个黄土夯成的圆台上。磨盘是青灰色的,沉甸甸地卧在那里,两扇磨盘咬合处,那螺旋状的豁口,像一道道刻满符咒的路径,深奥而冷酷。仿佛不是由两扇青石凿成的,倒像是时光用无声的岁月浇铸的一枚沉重印章,深深地钤在黄土高原那片苍茫而又温暖的扉页上。它的每一次转动,都不是空转,而是在生活这本厚重的书上,清晰地印下一圈“生存”二字。我总觉得,那里面住着一个沉默的神灵,它吞吐着人间最质朴的馈赠,也掌控着一种循环往复的命运。 拉磨的是一头老实的毛驴,它永远戴着一副用破布缝成的眼罩。世界在它眼前缩小为一片无尽的黑暗,于是它的一生,便只剩下那一个被缰绳规定的圆。蹄声“嗒嗒”,不紧不慢,合着石磨“嗡嗡”的沉吟,成了我们村落最恒久的背景音。奶奶就坐在磨旁的一只小马扎上,手里拿着一把小笤帚,不时将溢到磨边的粮粉扫回去。她的身影在毛驴周而复始的步履里,显得那么安详,又那么坚定。 麦子、荞麦、金黄的谷子,从磨顶的孔眼里瀑布般地灌进去,随即被那无情的石齿咬住、碾碎。起初是“沙沙”的破裂声,像一场细密的雨;接着,便成了“嗡嗡”的摩擦声,浑厚而绵长。那一刻,我仿佛能听见每一粒粮食的梦被碾碎的声音,它们告别了作为种子的完整,在一种近乎暴烈的碾压中,升华成纷纷扬扬的雪白。奶奶说:“瞧,它们疼过这一回,才能变成养人的吃食。” 那时我不懂,只觉得这过程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。而今回想,那何尝不是这片土地上万物生存的隐喻?就像那拉着磨的毛驴,用一生的辛苦画着一个看不见尽头的圆;就像我的奶奶,将青春、汗水乃至整个生命,都无声地填入这生活的磨盘。没有呐喊,没有抱怨,只有日复一日的承受与转化,在艰辛里磨出生活本身的滋味。 磨好的面粉,带着石头的体温和谷物的精魂,被奶奶小心翼翼地收进面袋。那晚的饭食,必定是格外香甜的。或是新麦烙的饼,咬一口,满嘴是阳光的醇厚;或是荞麦做的面节节,被浆水包裹着,能一直暖到心底。那种由口舌弥漫至全身心的满足,是一种根植于大地的、最扎实的幸福。它不来自索取,而来自创造;不来自享用,而来自亲身参与的、完整的劳动过程。 后来,电动的钢磨取代了石磨,它更快,更白,更省力。毛驴卸下了眼罩,却似乎也迷失了方向。那个黄土的磨台渐渐荒芜,磨坊的土坯顶也被岁月卷走了,石磨在风雨中彻底沉默,磨眼里,甚至长出了倔强的草。 我站在冰冷的钢磨前,再也闻不到那混着石头与汗水气息的面香。时代向前奔涌,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便捷与温暖,可那份从艰辛劳作中亲手酿造出的满足感,那份看着原材料在自己眼前完成生命蜕变的幸福感,却也一同被碾碎,飘散在往昔的风里了。 如今,奶奶也已故去多年。我闭上眼,她仿佛还坐在那磨盘边,灰白的头发在风里拂动,哼着那支没有歌词的曲调。那石磨转动的嗡嗡声,毛驴的蹄声,和她温柔的哼唱,交织成一条河流,在我生命的河床上静静流淌。我才明白,我思念的,不只是一盘石磨,更是那围绕石磨所构建的一整个温暖、缓慢而坚韧的世界。在那个世界里,辛苦与幸福是如此紧密地交融,就像磨盘上那来回交替的豁口,它们共同碾出的,是生活最本真、最醇厚的味道。 那味道,是黄土地的魂魄,是亲人的温度,是一个时代沉默而坚强的背影。它告诉我,所有看似循环往复的艰辛,终将在时间的磨盘下,化为供养我们精神的、最洁白的食粮。(责任编辑 蒲玉凤) | |
|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 |
| 浏览次数: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