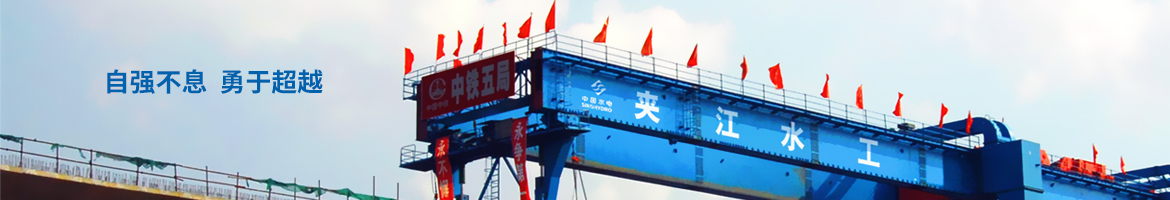缺口 | |
| |
南国的重阳总是湿冷,风里带着水汽,全无故乡的筋骨。每逢此日,记忆便被撬开一道缝,显现出白草塬上九月九的光影声色来。 记忆里的白草塬,是被秋风洗过的。那时的天蓝得不容分说,塬上的土黄得厚重,一场庙会,便像是一匹沉黯的粗布上,忽然泼满了浓烈斑斓的颜料。锣鼓家伙的声浪,能传出好几里地去。我被父亲架在肩头,人潮像温热的暖流,裹挟着我们向前。空气里的复杂是独属于乡野盛会的味道:香烛的烟火气。 而在这一切之上,有一种味道,对于当时的小孩而言,是直击魂魄的,那便是“鸡翅膀”的香。其实,它不过是裹着辣椒面与香料的面筋,因形得名。可那却是我童年认知里的佳肴。我总是死死攥着母亲的衣角,把她拽到那个支着玻璃匣子的小摊前,眼巴巴地望进去,看着那让人嘴馋的红色板状物。母亲总会一边说着“这有啥好吃的”,一边还是从兜里摸出几张钱。当那油滋滋、咸辣辣的“鸡翅膀”落到手里,一口咬下,那股子霸道而廉价的香,便从舌尖一路烧到胃里,是足以让整个世界都黯然失色的满足。 光有“鸡翅膀”还不够,还得配“汽水”。那装在透明袋子里的橘色甜水,一仰头,气泡便凶猛地蹿上来,直冲天灵盖,辣得人眼泪直流,却又通体舒泰。我常常一手举着辣条,一手提着汽水袋,觉得自己是这庙会上混的最好的。 孩子的荒唐,总在饱足后滋生。有一年,竟和玩伴偷溜去后山掏鸟窝,正当我们为一个草窝里的发现而惊喜低呼时,一声炸雷般的怒吼在身后响起:“碎怂!不要命了!”回头一看,是父亲铁青的脸。那一次,我被父亲像拎小鸡一样拎回家,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扫帚疙瘩。母亲在一旁,想劝又不能劝,只背过身去。那木棍抽在腿上的火辣,与“鸡翅膀”的辣,竟是童年两种最真切的滋味。后来才明白,父母怕的不是我们弄脏衣服,是怕我们惊了山里的长虫,怕我们从不高的土崖上失足,那顿“扫帚伺候”,里面是揉碎了的担忧与后怕。 那时的痛,是真切的;那时的委屈,也是天大的。哪里能想到,这痛与委屈,竟也会在岁月的酿造下,变成一壶回甘的酒。 如今,我身处千里之外的海边大都市,可以买下整排货架的辣条,喝到各种各样的汽水。可“鸡翅膀”失了魂魄,汽水只剩甜腻。至于山,是温顺的土丘,再无那般野趣。 重阳节又至,古人于此日登高、佩茱萸、饮菊酒,是为辟邪求祥。而我,这个远方的游子,只能在这南国的土地,登高北望。我望得见什么呢?望得见白草塬上那轮比这里清冷得多的月亮,望得见庙会散场后空荡荡的戏台,望得见老屋里那柄倚在门后的已磨秃了的旧扫帚。 那根辣条的咸辣,那顿扫帚的火辣,原来都是故乡烙在我身上的印记。平日里不痛不痒,只在这秋风起时,才猛地发作起来,提醒着我的来路,也明示着我的去途。 他乡的圆满里,总有个填不满的缺口。那缺口,是再多的“鸡翅膀”,也填不回来了。(责任编辑 蒲玉凤) | |
|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 |
| 浏览次数: |